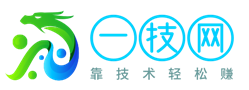上海,始終是女性議題生發(fā)和文藝創(chuàng)新的先鋒陣地。從王安憶、奚美娟到朱潔靜、柳鳴,從袁雪芬、陳薪伊到邵藝輝、周可,一代又一代的女性文藝工作者在這里生長(zhǎng)、出發(fā)、閃耀。開(kāi)放多元、兼容并包的城市文化,不僅給予女性文藝工作者以自由發(fā)展的舞臺(tái),更是她們創(chuàng)造性思維的源泉,同時(shí)也以她們的作品和表達(dá),參與塑造著這座城市的品格。她們以上海為支撐,以文藝為舟楫,引領(lǐng)著我們駛向更為遼闊、更為和諧的文明海洋。
在第115個(gè)國(guó)際勞動(dòng)?jì)D女節(jié)來(lái)臨之際,澎湃新聞上海文藝推出“伊的藝術(shù)”專題,從文學(xué)、影視、戲劇、舞蹈、古典樂(lè)、音樂(lè)劇、脫口秀、藝術(shù)展覽等8個(gè)領(lǐng)域,集中呈現(xiàn)近年來(lái)上海女性文藝面貌,向全體女性文藝工作者致敬,向她們杰出的工作致敬,向始終致力于各個(gè)領(lǐng)域的性別平等,消除偏見(jiàn)和歧視,致力于加深文明圖景的所有行動(dòng)者、發(fā)聲者、擁護(hù)者,致以深深的敬意。
上海,這座充滿魅力與活力的國(guó)際化大都市,在舞蹈藝術(shù)領(lǐng)域一直走在前沿,而女性力量在其中更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。近年來(lái),上海的女性舞蹈藝術(shù)家們以她們的才華、熱情和堅(jiān)韌,創(chuàng)作了眾多以女性為主題的舞蹈藝術(shù)作品,不僅豐富了上海的舞蹈藝術(shù)景觀,也為中國(guó)乃至世界的舞蹈事業(yè)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思想。
在正式的敘述之前,有必要先“疊個(gè)甲”。任何的梳理或盤點(diǎn),都難免有掛一漏萬(wàn)之弊。當(dāng)下上海的女性舞蹈藝術(shù)家不知凡幾,難以一一細(xì)數(shù)。而筆者也只能通過(guò)自己有限的目光,對(duì)近年來(lái)自己較有感觸的一些作品與人物,以及一些現(xiàn)象加以敘述,希望可以管中窺豹,從中映射出當(dāng)下上海舞蹈界的女性力量。其中的疏漏,自然應(yīng)歸咎于筆者視野的促狹。而上海作為國(guó)際國(guó)內(nèi)極為重要的演出市場(chǎng),國(guó)內(nèi)外演出云集于此,其中雖不乏女性題材的精品力作,但因其與上海城市并無(wú)過(guò)多關(guān)聯(lián),故也不必分散筆力加以詳述。此外,本文所論及的還是集中在舞蹈的表演與創(chuàng)作,對(duì)于在上海界眾多的女性舞蹈教育者也只能忍痛割舍。但值此“三八”國(guó)際婦女節(jié)之際,仍要為這些辛勤耕耘的女“園丁”們致以崇高的敬意,如果沒(méi)有她們,恐怕也難有當(dāng)下上海舞蹈市場(chǎng)的繁榮。

2024年上海國(guó)際藝術(shù)節(jié)開(kāi)幕演出,上海歌舞團(tuán)舞劇《李清照》劇照
舞劇中的女性:傳說(shuō)與文學(xué)、歷史與現(xiàn)實(shí)交織
回望近五六年上海出品的大型舞劇,聚焦女性人物,或是女性相關(guān)主題的作品涌現(xiàn)了不少精品佳作。從2019年上海芭蕾舞團(tuán)推出的芭蕾舞劇《茶花女》到2024年上海歌舞團(tuán)創(chuàng)制的新“國(guó)風(fēng)”舞劇《李清照》,傳說(shuō)與文學(xué)、現(xiàn)實(shí)與歷史中的女性交替登臺(tái),用她們的境遇與命運(yùn)、困惑與新生,展現(xiàn)出女性的生命厚度與廣度,彰顯了女性的力量與品格。
2019年,由上海芭蕾舞團(tuán)創(chuàng)作的芭蕾舞劇《茶花女》首演問(wèn)世。該劇以小仲馬同名世界文學(xué)名著為創(chuàng)作藍(lán)本,講述了發(fā)生在法國(guó)七月王朝背景下的悲劇故事:為生計(jì)而淪為上流社會(huì)交際花的瑪格麗特與男主角阿爾芒相愛(ài),卻因階級(jí)身份的差異被拆散,貴族階級(jí)道德觀念的禁錮、諸多誤會(huì)和不解成為二人相愛(ài)的羈絆,瑪格麗特最終患病離去。作品運(yùn)用倒敘的手法,以女主角瑪格麗特生命的彌留之際作為故事的開(kāi)端,由此引出瑪格麗特與男主角阿爾芒之間沖破世俗、真摯熱烈卻又波折無(wú)奈的愛(ài)情故事,展現(xiàn)了她充滿悲劇色彩的人生。原著小說(shuō)中所描寫的瑪格麗特企圖沖破各種社會(huì)桎梏追求自身幸福的愛(ài)情悲劇,揭示出彼時(shí)法國(guó)男權(quán)社會(huì)下的女性意識(shí)覺(jué)醒,使得這部作品充滿了關(guān)懷女性的底色。而上芭團(tuán)隊(duì)的精彩演繹與華美舞臺(tái)呈現(xiàn),也讓人更加感懷作品中的女性悲劇。

舞劇《嫦娥》劇照
上海歌劇院舞劇團(tuán)2020年推出的舞劇《嫦娥》則取材中國(guó)傳統(tǒng)神話,以現(xiàn)代人的視角對(duì)“嫦娥奔月”的傳說(shuō)故事進(jìn)行了重新解讀。作品講述了嫦娥與后羿動(dòng)人的愛(ài)情故事,以及嫦娥為了避免民眾不受黑暗侵蝕,被迫吞下靈藥飛升月宮,展現(xiàn)出其“為大愛(ài)舍小愛(ài)”的擔(dān)當(dāng)。創(chuàng)作者有意聚焦于“嫦娥”人物本身和她內(nèi)心的情感之路,并以月的“陰晴圓缺”為喻,與劇中嫦娥的“悲歡離合”遙相呼應(yīng),讓“嫦娥”與現(xiàn)代的觀眾產(chǎn)生更多情感上的連接和共鳴。
如果單純從女性主體性的角度來(lái)看,這兩部雖然都以女性人物的命運(yùn)作為敘事脈絡(luò),但人物形象更多停留在“犧牲者”和“神女”的傳統(tǒng)性別形象,女性人物的復(fù)雜性和人物弧光都略顯不足。相較之下,后續(xù)的幾部女性題材舞劇則完成了女性自我意識(shí)從自在到自覺(jué)的轉(zhuǎn)變,在展現(xiàn)了女性的力量與命運(yùn)的同時(shí),也可從中清晰地看到女性主體自覺(jué)與復(fù)雜境遇。

舞劇《白蛇》劇照
由上海大劇院出品的舞劇《白蛇》于2022年首演,并于2025年改編復(fù)演。作品雖然以經(jīng)典傳說(shuō)為名,但其內(nèi)容則是當(dāng)代女性自我意識(shí)覺(jué)醒、追求自由的故事。據(jù)說(shuō),該劇源于三個(gè)女人的一拍即合——芭蕾藝術(shù)家譚元元、上海大劇院總經(jīng)理張笑丁、戲劇導(dǎo)演周可共同看到了“白蛇”故事本身跨越時(shí)代的生命力:白蛇對(duì)于“人性”的主動(dòng)追求,對(duì)于“人妖殊途”之清規(guī)戒律的主動(dòng)抗?fàn)帲词狗胖迷诋?dāng)代語(yǔ)境中,依然可以與現(xiàn)實(shí)生活同頻共振。神話傳說(shuō)中的白蛇、許仙、法海三人分別對(duì)應(yīng)劇中妻子、丈夫和心理醫(yī)生的角色,而青蛇則成為妻子內(nèi)心的另一重人格,象征著妻子未被馴服的原始欲望與未完成的自我。借由古與今、現(xiàn)實(shí)與夢(mèng)境兩個(gè)時(shí)空的不斷轉(zhuǎn)化,不斷喚醒妻子內(nèi)心深處對(duì)于自由、獨(dú)立和本真自我的向往,從而展示了女性從迷失、懷疑到接納自我的過(guò)程,并以此來(lái)嘗試探索女性的心靈與精神。作品最后,象征禁錮的雷峰塔始終未曾真正倒塌,也揭示了當(dāng)代女性所面臨的現(xiàn)實(shí)境遇。但正如該劇宣傳語(yǔ)“我們終將成為自己”所展示的,處于困境中的女性仍在堅(jiān)持著對(duì)自我的追尋,不曾停歇。
上海歌舞團(tuán)2024年創(chuàng)演的新“國(guó)風(fēng)”舞劇《李清照》將目光聚焦到了有“千古詞宗”之譽(yù)的歷史人物李清照身上,展示了她波瀾壯闊的一生。通觀全劇,可以清晰地看到李清照從不識(shí)愁滋味的閨中少女,到賭書潑茶、志趣相投的夫妻情深,再到家國(guó)情懷覺(jué)醒、“倜儻,有丈夫氣”的女中豪杰的人物成長(zhǎng)弧光。劇中上半場(chǎng)內(nèi)容充分展現(xiàn)了李清照與趙明誠(chéng)二人相識(shí)、相戀的過(guò)程,以及二人“以書為媒”、金石收錄、文脈傳承的婚后生活。但到了上半場(chǎng)的末節(jié)“南歌子·南渡”,北宋國(guó)破,李清照南遷沿途所見(jiàn)均是因家國(guó)離亂而帶來(lái)的民不聊生,激起了她的無(wú)盡感懷,進(jìn)而吟詠出了《夏日絕句》這一千古絕唱,家國(guó)情懷漸漸覺(jué)醒。而下半場(chǎng)“武陵春·遇奸”“鷓鴣天·破繭”“丑奴兒·狀告”三個(gè)段落則算是全劇中敘事性最強(qiáng)的一組段落,簡(jiǎn)潔明快地呈現(xiàn)了李清照在病困之際再嫁張汝舟,后發(fā)現(xiàn)所托非人,勇敢主動(dòng)即使入獄也要離婚的這段經(jīng)歷。這一部分是對(duì)李清照角色成長(zhǎng)的人物弧光最集中的展現(xiàn)。對(duì)于封建時(shí)代的女性而言,主動(dòng)離婚不僅需要相當(dāng)?shù)挠職猓簿哂泻艽蟮碾y度。而李清照對(duì)于此事的毅然決然,直面身陷囹圄的牢獄之災(zāi)也在所不惜,由此亦可見(jiàn)劇中李清照這一角色的自主精神。更值得一提的是,在“丑奴兒·狀告”一段中,李清照擊鼓時(shí)所接受審判的不僅有張汝舟,還有一眾貪官污吏,則將本段的意指進(jìn)一步深化,其批判的矛頭不光指向惡夫,更指向了那些造成國(guó)破民哀的昏庸官吏們,從而凸顯了李清照的家國(guó)情懷、果敢堅(jiān)強(qiáng)。
傳承與破圈:劇場(chǎng)內(nèi)外的女舞者們
舞臺(tái)上的女性角色多姿多彩,而臺(tái)下女性舞蹈家的故事同樣熠熠生輝。上述幾部作品中的主角譚元元、朱潔靜、戚冰雪分別是70后、80后、90后,順次串聯(lián)起當(dāng)今活躍在上海舞臺(tái)上的女性舞者的脈絡(luò)譜系,或可以此為例透視上海女性舞者的群像。這三位舞者的經(jīng)典舞臺(tái)形象和精彩人生,在大眾傳媒中已經(jīng)有大量長(zhǎng)篇累牘的報(bào)道,被一再述說(shuō),在此也毋庸贅述。筆者更在意的,是她們所展現(xiàn)出來(lái)的上海女性舞者的傳承,以及她們近年來(lái)在劇場(chǎng)內(nèi)外所做的諸多破圈的努力與嘗試。

舞劇《白蛇》劇照
被觀眾愛(ài)稱為“上海小囡”的譚元元是中國(guó)舞者走向世界的一個(gè)代表。這位舊金山芭蕾舞團(tuán)曾經(jīng)最年輕的首席舞者,同時(shí)也是第一位華裔首席舞者,用她舞臺(tái)上精彩絕倫的表演,征服了全世界的觀眾,也擊退了國(guó)際上對(duì)于華人舞者的傲慢與偏見(jiàn),為一眾后輩闖蕩國(guó)際舞壇樹立了榜樣。2014年,譚元元完成了在舊金山芭蕾舞團(tuán)的告別演出,將工作和生活的重心逐漸轉(zhuǎn)回國(guó)內(nèi),不僅與上海大劇院合作出品舞劇《白蛇》,還同時(shí)擔(dān)任上海戲劇學(xué)院舞蹈協(xié)同創(chuàng)新中心主任、蘇州芭蕾舞團(tuán)藝術(shù)總監(jiān),在舞者之外增添了創(chuàng)作者和教育者的身份。如今的譚元元,一方面開(kāi)展創(chuàng)作,期待帶領(lǐng)年輕的中國(guó)舞者走向更廣闊的世界舞臺(tái);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國(guó)際影響力為國(guó)內(nèi)的芭蕾創(chuàng)作與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匯聚資源,并將自己多年表演的藝術(shù)感悟、闖蕩國(guó)際舞壇的經(jīng)驗(yàn)體會(huì)傳遞給新一代的年輕舞者們。同時(shí),她也依然在磨煉和等待著,希望有一天能再遇到合適的作品、合適的角色,重新登上舞臺(tái)。
朱潔靜同樣在經(jīng)歷職業(yè)生涯角色的轉(zhuǎn)換。之前作為演員的她,關(guān)注的是如何在舞臺(tái)上鮮活生動(dòng)地呈現(xiàn)出作品與人物。《霸王別姬》中的“虞姬”、《朱鹮》中的“鹮仙”、《永不消逝的電波》中的“蘭芬”,以及《李清照》中的“李清照”,這一個(gè)個(gè)性格迥異、截然不同的人物角色,在朱潔靜的詮釋演繹之下,躍然舞臺(tái)之上,展現(xiàn)出各不相同,但又同樣極富魅力的女性形象。其在2023年以舞者身份斬獲第32屆“上海白玉蘭戲劇表演藝術(shù)獎(jiǎng)”主角獎(jiǎng)榜首的桂冠,也正是對(duì)她在舞臺(tái)表演上能力的充分肯定。而現(xiàn)在的朱潔靜,不僅是上海歌舞團(tuán)的榮典·首席演員,同時(shí)也是團(tuán)里的副團(tuán)長(zhǎng),除了繼續(xù)在她所熱愛(ài)的舞臺(tái)上發(fā)光發(fā)熱之外,也承擔(dān)起帶領(lǐng)團(tuán)隊(duì)、引領(lǐng)后輩的責(zé)任。從單純的演員,到團(tuán)隊(duì)的管理者,這曾是許多前輩舞者走過(guò)的道路。這不僅是一種身份的進(jìn)階,同時(shí)也是舞者世代繼替的表現(xiàn)。如今看著自己曾經(jīng)那些經(jīng)典角色逐一都有了接棒的年輕演員,朱潔靜也樂(lè)于去陪伴著團(tuán)里的年輕演員們成長(zhǎng),幫助他們?nèi)パ堇[屬于自己的華美篇章。

舞劇《歌劇魅影》劇照
相比于前述二人逐漸步入職業(yè)生涯的后半程,剛剛獲得2024年度全國(guó)三八紅旗手榮譽(yù)的戚冰雪則屬于職業(yè)生涯的正當(dāng)年。2014年進(jìn)入上海芭蕾舞團(tuán)的戚冰雪,進(jìn)團(tuán)后一步一個(gè)腳印,不僅在北京國(guó)際芭蕾舞比賽、上海國(guó)際芭蕾舞比賽、中國(guó)舞蹈“荷花獎(jiǎng)”舞劇評(píng)獎(jiǎng)等重要賽事中摘得重量級(jí)獎(jiǎng)項(xiàng),并且在《長(zhǎng)恨歌》《吉賽爾》《天鵝湖》《梁山伯與祝英臺(tái)》《寶塔山》《歌劇魅影》《睡美人》《茶花女》等作品中擔(dān)綱主演。在成功的背后,除了她自己的刻苦努力外,同樣也濃縮著院團(tuán)對(duì)于年輕人才培養(yǎng)的支持,是一代代舞者的傳承與延續(xù)。前輩舞者的言傳身教,以老帶新、以戲帶人的培養(yǎng)體系,讓戚冰雪這樣的年輕舞者逐步成長(zhǎng)為優(yōu)秀的新生力量。而她也啟迪著團(tuán)里的小演員們。
雖然這三位舞者之間并沒(méi)有直接的傳承關(guān)系,但是她們所代表的不同代際卻可以為我們勾勒出當(dāng)下上海女性舞者的傳承圖譜。每一代的舞者,都是上承前輩、下啟后輩,接棒站上舞臺(tái)中央。那些前輩們照在她們身上的光,最終讓她們自己也發(fā)出光來(lái)照耀后輩,共同點(diǎn)亮了舞臺(tái)。而在傳承之外,這幾位女舞者也都努力破圈,讓舞蹈藝術(shù)與女性舞者為更廣泛的公眾所認(rèn)知。
談及破圈,自然繞不開(kāi)這幾位女舞者的“觸電”。三人都曾不約而同地走進(jìn)電視傳媒。比如三人都曾登上過(guò)央視春晚的舞臺(tái),讓許多不曾走進(jìn)劇場(chǎng)的國(guó)人感受到舞蹈藝術(shù)的魅力與女性舞者的風(fēng)姿。早在1994年,年僅18歲的譚元元就曾在春晚上表演,以此為始,她先后四次踏上春晚舞臺(tái)。從最初的芭蕾雙人舞,到2025年具有東方氣韻的《伊人》,一路走來(lái)也見(jiàn)證了譚元元的自我成長(zhǎng)與審美追求。朱潔靜也是同樣四登春晚。《晨光曲》《朱鹮》《碇步橋》《幽蘭》四個(gè)作品接連演繹出中國(guó)舞獨(dú)有的身韻與柔美。而戚冰雪則是在2024年在春晚舞臺(tái)上領(lǐng)銜表演了芭蕾《鵝鵝鵝》,向全國(guó)觀眾展示了海派芭蕾的獨(dú)特魅力。此外,譚元元與朱潔靜還參加了《舞蹈風(fēng)暴》《乘風(fēng)破浪的姐姐》等綜藝節(jié)目,讓更多人能夠了解舞蹈演員背后的熱愛(ài)與堅(jiān)持,也讓我們看到女性舞者更多樣的風(fēng)采。這些在大眾傳媒上的嘗試,折射出的是當(dāng)下女性舞者的不斷自我突破與探索。她們不僅在劇場(chǎng)內(nèi)去塑造經(jīng)典的舞臺(tái)形象,同時(shí)也走出劇場(chǎng)、走向大眾,讓更多人可以感受舞蹈,看見(jiàn)藝術(shù)內(nèi)外的女性。
當(dāng)然,以上三位的故事只是活躍在劇場(chǎng)內(nèi)外的眾多上海女性舞者的縮影。辛麗麗、季萍萍、范曉楓、宋潔、譚一梅、畢瑩、于婷婷、周曉輝、馮子純、郭文槿……一代又一代的上海女性舞者在臺(tái)上臺(tái)下綻放光芒,用她們出彩的人生和精湛的表演,譜寫出屬于女性舞蹈家的精彩華章。
女性表達(dá)與表達(dá)女性:現(xiàn)當(dāng)代舞蹈劇場(chǎng)中的女性創(chuàng)作
上海一直都是中國(guó)女性現(xiàn)當(dāng)代舞創(chuàng)作與表演的前沿。早在90年代末,中國(guó)最早的民營(yíng)現(xiàn)代舞團(tuán)金星舞蹈團(tuán)便成立于上海,其一系列的創(chuàng)作都以其鮮明的自我意識(shí)和獨(dú)特的藝術(shù)表達(dá)都令觀眾耳目一新。彼時(shí)現(xiàn)代舞在中國(guó)內(nèi)地尚屬新生,女性的創(chuàng)作者和表演者在上海亦是寥寥。而如今在上海的舞臺(tái)上,女性現(xiàn)當(dāng)代舞創(chuàng)作者層出不窮,不斷用作品向觀眾傳遞著來(lái)自女性對(duì)世界的認(rèn)知與思考,也引導(dǎo)觀眾去更多地關(guān)注女性的困惑及其所處的境遇。
在當(dāng)下上海舞蹈界一眾女性現(xiàn)當(dāng)代舞創(chuàng)作者中,謝欣無(wú)疑是極具代表性的一位。2014年,在國(guó)內(nèi)外屢獲殊榮的謝欣在上海創(chuàng)立了謝欣舞蹈劇場(chǎng),開(kāi)展創(chuàng)作與演出,其出眾的身體技巧及對(duì)舞蹈美學(xué)的獨(dú)特思考,逐漸被業(yè)界和觀眾廣泛認(rèn)可和贊譽(yù)。近年來(lái),謝欣除了帶領(lǐng)團(tuán)隊(duì)繼續(xù)深耕劇場(chǎng)、持續(xù)創(chuàng)作之外,也廣泛亮相大眾傳媒,相繼參加了《舞蹈風(fēng)暴》《乘風(fēng)破浪的姐姐》等電視綜藝。同時(shí),她還從上海走向世界,帶團(tuán)赴歐洲多國(guó)巡演。而她本人也先后接到威尼斯雙年展、巴黎歌劇院等的委約創(chuàng)作,是巴黎歌劇院歷史上首位獲得委約的中國(guó)女性編舞家。但也就在2023年底,一場(chǎng)突如其來(lái)的大火將謝欣舞蹈劇場(chǎng)所在的排練廳燒成灰燼。經(jīng)歷了這場(chǎng)沉重打擊的謝欣將災(zāi)禍化為創(chuàng)作動(dòng)力,在今年和女性音樂(lè)家付藝霏合作演繹音樂(lè)舞蹈劇場(chǎng)《薩蒂之名·春之祭》,昭示其與舞團(tuán)的浴火重生。

《薩蒂之名》劇照
在筆者看來(lái),謝欣更類似于女性表達(dá)者,而非表達(dá)女性者。其創(chuàng)作并沒(méi)有刻意去突顯自己的女性主體身份,而是從自我對(duì)世界的感知以及個(gè)體的生命歷程出發(fā),在身體的節(jié)律呼吸中去展現(xiàn)創(chuàng)作者對(duì)外部世界的敏感觀察與內(nèi)心的細(xì)膩情感,從而形成了自己獨(dú)具一格的肢體語(yǔ)匯與舞臺(tái)風(fēng)格。比如,《一撇一捺》是用身體去拆解“人”字,探究人之為人的情感與連接;《未·知》是用現(xiàn)代舞藝術(shù)去表達(dá)對(duì)生活和未來(lái)的探索;《執(zhí)迷》是對(duì)人精神中的執(zhí)著與沉迷的具象化呈現(xiàn);《靜地回升》是關(guān)注記憶與時(shí)間,回溯自己生命歷程中的愛(ài)與痛;《九重奏》是展現(xiàn)人與空間的關(guān)系,用肢體語(yǔ)匯呈現(xiàn)獨(dú)特的物理美學(xué);《薩蒂之名·春之祭》則是改編經(jīng)典,去思辨生命的輕與重,表達(dá)向死而生的生命活力。但這并不意味著謝欣及其團(tuán)隊(duì)就沒(méi)有去關(guān)注女性的處境。比如在由謝欣舞蹈劇場(chǎng)出品,上海國(guó)際舞蹈中心劇場(chǎng)聯(lián)合制作的舞蹈劇場(chǎng)《方舟》中,創(chuàng)作者就分別用《此船由我建》和《最后的幸存者》兩部分內(nèi)容去聚焦夫妻親密關(guān)系以及人的自我認(rèn)知與感知世界間的碰撞,既表達(dá)了女性的境遇,也展現(xiàn)了女性藝術(shù)家對(duì)人生與世界的洞察。
同樣于2014年成立自己舞團(tuán)D.LAB DANCE的段婧婷在近兩年則是相繼推出了兩部具有鮮明性別意識(shí)、表達(dá)女性主體性的作品《裂縫》和《I am Fluid》,并且都采取了全女班的表演團(tuán)隊(duì)。其中,2023年的作品《裂縫》將女性生活中所經(jīng)歷的困境以及所面對(duì)的質(zhì)疑抽象為舞臺(tái)上無(wú)形的桎梏,并通過(guò)展現(xiàn)女舞者打破束縛,在裂縫中新生的形象以展示女性的主體性與力量。而2024年的作品《I am Fluid》,以舞蹈編排和影像敘事結(jié)合的方式,去捕捉不同女性個(gè)體在面對(duì)創(chuàng)傷與困境時(shí),打破自己、突破自己、最終接納自己的過(guò)程,以尋找自由表達(dá)女性力量的更多可能。舞蹈中的女性身體是柔軟的薄紗、是流動(dòng)的空氣、是山澗里的潺潺溪流,用自己的生命力量融匯成一條長(zhǎng)河,通往自己內(nèi)心的自由,釋放女性力量。正如段婧婷自己在作品詮釋中所言:“我們想傳遞的始終是,每一位女性都值得被看見(jiàn),無(wú)論是她們身上的高光還是柔軟”。
另一位女性編導(dǎo)江帆則采取了更為具象的方式來(lái)傳遞她的思考以及對(duì)女性群體的觀察。作為創(chuàng)作者,江帆的靈感始終來(lái)源于對(duì)世界與人的觀察,再借由舞蹈肢體對(duì)形象與情感加以表達(dá)。在她2017年的作品《流量》中,便展現(xiàn)了她對(duì)于網(wǎng)紅女主播的觀察,以演員身體為介質(zhì),去勾連劇場(chǎng)內(nèi)的觀眾與劇場(chǎng)外的蕓蕓女“網(wǎng)紅”們。而在2023年推出的《雜食動(dòng)物》中,江帆將觀察的目光聚焦在自己與個(gè)體女性身上,演繹了一場(chǎng)半自傳色彩的、將肢體和語(yǔ)言、虛構(gòu)和記錄相結(jié)合的獨(dú)白劇場(chǎng)。作品中女主人公胡豆子結(jié)束了10年的婚姻,在離婚所帶來(lái)的物質(zhì)獨(dú)立、情感空白的特殊時(shí)間節(jié)點(diǎn),試圖嘗試尋找新鮮多元的、尚未擁有過(guò)的精神獨(dú)立。在她的思考和回憶所喚起的女性眾生相中,既有女性在各個(gè)場(chǎng)域中必須面對(duì)甚至內(nèi)化的利益交換,也有作為“中女”需不斷克服的社會(huì)偏見(jiàn)和自我焦慮,還有來(lái)自妻子、女兒、自我等不同身份所帶來(lái)的自由、責(zé)任、親情、友情等各方面的糾結(jié)。
曾幾何時(shí),國(guó)內(nèi)不少女性舞者曾興起過(guò)一陣創(chuàng)制個(gè)人舞蹈劇場(chǎng)的熱潮,從中可以窺見(jiàn)女舞者們?cè)谠忈尳巧猓M栌晌璧杆囆g(shù)認(rèn)知世界與表達(dá)自我思考的趨向。相較而言,傳統(tǒng)的舞劇要兼顧故事劇情和場(chǎng)景呈現(xiàn),而現(xiàn)當(dāng)代舞領(lǐng)域的“舞蹈劇場(chǎng)”則更加突顯創(chuàng)作者的思考與表達(dá),為女性創(chuàng)作者提供更加自由和直抒胸臆的藝術(shù)空間,逐漸成為女性舞蹈編創(chuàng)者情感和思想呈現(xiàn)的實(shí)驗(yàn)場(chǎng)。上面列舉的幾位女編導(dǎo)正是這些女性創(chuàng)作者的縮影。她們或以自己獨(dú)特的女性感知去觀察生命與世界,或關(guān)注現(xiàn)實(shí)中的女性命運(yùn)與境遇。但無(wú)論是女性表達(dá)者還是表達(dá)女性者,她們都用自己的創(chuàng)作與思考向觀眾、向世人傳遞著屬于女性的藝術(shù)力量。
舞蹈藝術(shù)中女性力量興起的社會(huì)土壤
作為“亞洲演藝之都”,上海不僅是文化藝術(shù)交匯的碼頭,同時(shí)也是催生藝術(shù)創(chuàng)新發(fā)展的源頭。在這里,不僅可以廣泛看到國(guó)際國(guó)內(nèi)前沿多元的女性創(chuàng)作或女性題材舞蹈作品,同時(shí)為女性舞蹈家的藝術(shù)表達(dá)提供了良好的土壤。在這背后,重視文化藝術(shù)的政策支持自不待言,而來(lái)自市場(chǎng)多元主體有意識(shí)的投入也是其中一股重要的扶持力量。
以上海國(guó)際舞蹈中心為例。近年來(lái),上海國(guó)際舞蹈中心劇場(chǎng)先后引進(jìn)了比利時(shí)安娜·特蕾莎的《雨》、德國(guó)皮娜·鮑什的《春之祭》、南非杰曼·阿科尼的《禮敬先祖》、西班牙的拉法艾拉·卡拉斯科的《夜曲:失眠建筑群》等一系列國(guó)際頂級(jí)女性舞蹈家的名篇佳作,同時(shí)也匯聚了楊麗萍、錢秀蓮、侯瑩、王亞彬、余爾格、古佳妮、王夢(mèng)凡等國(guó)內(nèi)不同代際的女性舞蹈家的創(chuàng)新藝術(shù)作品,讓廣大上海觀眾欣賞到更加豐富多元的女性表達(dá)與女性視角。與此同時(shí),上海國(guó)際舞蹈中心還與眾多女性舞蹈家合作,通過(guò)聯(lián)合藝術(shù)家、委約創(chuàng)作、青年編導(dǎo)孵化等不同形式,支持女性藝術(shù)家的創(chuàng)作與自我表達(dá)。像前述的謝欣、段婧婷、江帆等女性創(chuàng)作者都是國(guó)舞劇場(chǎng)的聯(lián)合藝術(shù)家。而在近年來(lái)國(guó)舞劇場(chǎng)的委約、青孵作品中,女性創(chuàng)作者或者女性主題的舞蹈創(chuàng)新作品更是不勝枚舉。像國(guó)舞劇場(chǎng)2023年的委約作品,余爾格的《獻(xiàn)給愛(ài)米麗的一朵玫瑰花》,便運(yùn)用雜技與現(xiàn)代舞相融合的肢體表演形式,去展現(xiàn)一個(gè)女性的生命,追問(wèn)一個(gè)女人該如何活著。同年國(guó)舞劇場(chǎng)的另外一部委約作品,女性主題三部曲《20,30,40》則是一部全女性編導(dǎo)、全女性演員的舞蹈劇場(chǎng)作品,由王佳妮與王姝歡編導(dǎo)的《佳妮歡歡》、龔興興與詹驪編導(dǎo)的《GEN/根》和吳艷丹(Nunu Kong)編導(dǎo)的《烏迪》組成。這三部作品分別聚焦不同年齡段的女性,展現(xiàn)了她們?cè)诓煌松A段的困惑、追求和成長(zhǎng)。其中,《佳妮歡歡》用舞蹈展示了20歲的青春、自由與不拘,以無(wú)拘無(wú)束的姿態(tài)沖破一切劃定的圈圈,挑戰(zhàn)邊界,表達(dá)了創(chuàng)作者對(duì)青春的熱愛(ài)和對(duì)自由的追求;《GEN/根》以女性的小腹為動(dòng)機(jī),探討了女性在生育過(guò)程中的身體和心理變化,展現(xiàn)了女性在生育過(guò)程中的力量和美麗,以此鼓勵(lì)女性認(rèn)識(shí)、接受和熱愛(ài)自己;《烏迪》展現(xiàn)了40歲女性對(duì)自我生活的審思,透過(guò)主人公“烏迪”的視角對(duì)生命中的愛(ài)與告白,以及所有的離別產(chǎn)生新的讀解與感悟,即便仍舊有迷茫與愚笨,但依然掩蓋不住女性自我從身體向外傳遞的光能和對(duì)美好的追求。
而在劇場(chǎng)之外,上海眾多的文藝機(jī)構(gòu)也同樣在挖掘女性舞蹈創(chuàng)作的自我表達(dá)。比如像西岸美術(shù)館和蓬皮杜中心、開(kāi)云集團(tuán)就曾合作舉辦過(guò)三屆“躍動(dòng)她影在西岸”當(dāng)代舞蹈節(jié),以弘揚(yáng)女性在舞蹈和編舞領(lǐng)域的思考力與創(chuàng)造力,賦能女性藝術(shù)家,為其發(fā)聲,助其成長(zhǎng)。每屆活動(dòng)都會(huì)邀請(qǐng)三位來(lái)自中法兩國(guó),在身體探索上具有獨(dú)創(chuàng)性語(yǔ)匯的女性編舞家?guī)?lái)原創(chuàng)作品,探索她們具有多元化、創(chuàng)造性和啟發(fā)性的藝術(shù)世界,并推動(dòng)兩國(guó)文化藝術(shù)交流。包括法國(guó)的瑪?shù)贍?middot;莫尼耶、雷吉娜·紹皮諾、朱莉·妮奧奇,中國(guó)的文慧、段妮、史晶歆、古佳妮、王夢(mèng)凡等舞蹈藝術(shù)家都曾為其創(chuàng)作作品。喜馬拉雅美術(shù)館也曾在2022年攜手STUDIO K與戲劇工作室「高空拋物」,創(chuàng)作的素人肢體戲劇《關(guān)于女人的一些碎片》,通過(guò)11位來(lái)自各行各業(yè)的女性素人演員,以各自的身份,在舞臺(tái)上呈現(xiàn)真實(shí)的自我,真實(shí)的肢體,講述真實(shí)的生活。這些女性在舞臺(tái)上所呈現(xiàn)出的真實(shí)生命經(jīng)驗(yàn)不僅擁有特殊的質(zhì)感,同時(shí)也是不可替代的力量。
類似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。一座城市的文化藝術(shù)發(fā)展,離不開(kāi)其所根植的城市環(huán)境與土壤。正因?yàn)樯虾碛?ldquo;開(kāi)放,創(chuàng)新,包容”這一最鮮明的城市品格,使得它成為文化藝術(shù)的熱土,廣納國(guó)內(nèi)外文化藝術(shù)創(chuàng)新成果,為文化藝術(shù)的發(fā)展與創(chuàng)造提供優(yōu)渥的表達(dá)空間,才最終成就了上海女性舞蹈藝術(shù)家們今日的成就。換言之,當(dāng)下上海舞蹈界女性力量和女性表達(dá)的成長(zhǎng),也正是上海城市文化繁榮發(fā)展的碩果。無(wú)論是來(lái)自官方的政府支持,還是來(lái)自社會(huì)、市場(chǎng)的多元主體、機(jī)構(gòu)的參與,共同為女性舞蹈家的創(chuàng)作與表達(dá)搭建了堅(jiān)實(shí)的基礎(chǔ)。在此之上,一代代女性舞蹈家層出不窮,國(guó)內(nèi)外女性文藝創(chuàng)作匯聚交融,在上海灘共同編織出舞蹈藝術(shù)中屬于女性的華美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