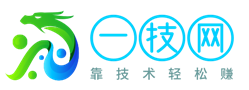李六乙導(dǎo)演作品話劇《雷雨》,此前于2月21日至23日在上海大劇院演出,后于3月5日至9日,在香港藝術(shù)節(jié)上演。兩次演出,作品因改編和表演等因素,口碑呈現(xiàn)兩極分化,喜歡者贊其“先鋒”“超前”,批評者則憤怒其“毀經(jīng)典”。澎湃新聞·上海文藝特約兩位作者從不同維度對本作進(jìn)行了解讀。
香港藝術(shù)節(jié)委約作品、李六乙導(dǎo)演的新版《雷雨》在上海演出之前,網(wǎng)上已有不少評論。原想《雷雨》這樣的經(jīng)典劇目,無論守正還是出奇,總不至于有太傷筋動(dòng)骨的變動(dòng)。其次,媒體上也有評論將演出形容得優(yōu)美詩意,令人神往。第三,報(bào)道說本次據(jù)1936年的單行本排演,“回到曹禺、回到文學(xué)、回到戲劇本身”是創(chuàng)作主旨,而且“這不僅是對原著的再現(xiàn),更是一次對中國戲劇美學(xué)形態(tài)的深刻反思與重建,進(jìn)而建立起這個(gè)時(shí)代的表演哲學(xué)”。如此一來,自然期待。
之前寫過,《雷雨》最動(dòng)人之處,是在舞臺上元?dú)饬芾斓爻尸F(xiàn)倫理秩序與生命激情之間的沖突,由此產(chǎn)生悲劇的審美能量。但今天,原作里壓抑郁熱的氛圍、亟須沖破的枷鎖,未必能獲得互聯(lián)網(wǎng)時(shí)代的感知與理解;人物在倫理困境、極端人性與殘酷命運(yùn)之間的審美張力,如今看來或許也會有些費(fèi)解和松弛;有些臺詞和場面,如天真的周沖對魯大海說“我能跟你拉拉手嗎?”之類,更時(shí)常會引發(fā)年輕觀眾的笑場。這都是近年來反復(fù)探討的問題,雖然刻意迎合市場并不足取,但創(chuàng)新呈現(xiàn)也確實(shí)需要。
看完全劇,并回味數(shù)天之后,試從舞臺、手法、表演和人物四方面來分析其得失與不足。

創(chuàng)新的得失:敘事與舞臺
其實(shí)早在2003年徐曉鐘導(dǎo)演、一眾戲劇梅花獎(jiǎng)得主表演的版本中,《雷雨》劇本原作里的序幕和尾聲就已曾恢復(fù),而且腳本忠實(shí)、表演扎實(shí),沒有刪減,時(shí)長300分鐘。這次李六乙版雖名義上恢復(fù)了序幕和尾聲,但其實(shí)與原著里差別甚大,其他改動(dòng)也不少,如將魯貴這一人物完全刪除等,因此宣傳中“回到原典”等說法實(shí)難成立。縱觀全劇,標(biāo)新立異之處甚多,有鮮明的實(shí)驗(yàn)色彩。可惜的是,這些大破大立的改動(dòng)并未減少時(shí)長,最后恰好也是300分鐘,觀之卻時(shí)有散亂、冗長和乏味之感。
曹禺本人曾為了在演出時(shí)保留序幕和尾聲兩段,試圖對第四幕作出刪減,但沒有成功,可見劇本的渾然一體使刪削實(shí)非易事。魯貴雖非主要人物,但在劇中各處起到重要的穿針引線和烘托對照作用,既是不少戲劇情節(jié)的樞紐,也以自身市儈的個(gè)性和行為參與其他角色的塑造,因此對魯貴的刪除勢必會引發(fā)情節(jié)上的費(fèi)解,造成不連貫的斷裂印象,以及其他角色在語言、動(dòng)作和情感等細(xì)節(jié)上的突兀感受。

空曠的舞臺設(shè)計(jì)和其他演員的始終在場
有評論說,此版《雷雨》需要觀眾對劇情非常熟悉,否則會看不懂。確實(shí),這種敘事的破碎感和戲劇張力的消除感自序幕之后逐漸明確,尤其到下半場,不少本該強(qiáng)有力的地方似乎總被抽空,重大的倫理沖突和情感震蕩所引發(fā)的緊張、崩塌、扣人心弦等傳統(tǒng)戲劇性的所在似乎都被散漫平淡的表演消除了,第四幕結(jié)尾的處理尤其讓人費(fèi)解。如此一來,不熟悉的觀眾自然感到莫名其妙、不得要領(lǐng),熟悉的觀眾也只聽到密集飛滾的臺詞,不斷落空預(yù)期。
有人說這是刻意為之的反戲劇、反敘事的先鋒手法。如果結(jié)合單一的極簡布景、演員的始終在場和雜亂的舞臺走位等特征來考量,似乎確有幾分類似追求。但《雷雨》是否適合反戲劇呈現(xiàn),怎樣處理較為適宜,如何從表演上落實(shí)這一宗旨,這都需要進(jìn)一步探究。
整個(gè)舞臺空間自始至終沒有任何變化,整體上如冰冷抑郁的牢獄,原作里不斷出現(xiàn)、烘托劇情的雷雨聲也堅(jiān)決不出現(xiàn),可見主創(chuàng)在視聽方面在竭力擺脫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風(fēng)格,有趣的是身后的幾位本地老年戲迷不停念叨,這舞臺設(shè)計(jì)真是太“做人家”(上海話節(jié)儉)、太會省工本了。其實(shí)極簡也好、表現(xiàn)主義也罷,甚至反敘事的想法都沒問題,因?yàn)檫@些先鋒手法,在西方戲劇已有起碼五六十年的歷史,如能處置巧妙得當(dāng),則既能突出周公館如深淵般的幽暗,也能營造身處夢境或意識深處的感官幻覺。同樣,一桌二椅的戲曲式空蕩舞臺,本來也可使演員獲得聚焦,讓其獲得更多發(fā)揮空間,但反過來也更考驗(yàn)表演的層次與功底。不過,當(dāng)?shù)谌坏攸c(diǎn)從周公館轉(zhuǎn)為魯家時(shí),這依然不變的布景多少有些怪異和潦草。

用轉(zhuǎn)椅和燈光從舞臺上分割出一個(gè)前臺
值得一提的是,舞臺上還用一把轉(zhuǎn)椅分割出一塊前臺,讓候場的周樸園坐著,與正在演戲的舞臺拉開時(shí)空距離和心理距離。演員始終在場的設(shè)計(jì)其實(shí)頗有匠心,能產(chǎn)生強(qiáng)烈的間離效果:觀眾觀看舞臺,舞臺上候場的角色也注視著場上人物正進(jìn)行的表演,且還有輕微的反應(yīng)和動(dòng)作。如周沖向繁漪訴說對四鳳的愛情時(shí),舞臺邊上候場的四鳳不斷在后方徘徊,時(shí)而為他們的對話而轉(zhuǎn)身,體現(xiàn)劇本上沒有的情感波瀾。周樸園訓(xùn)斥周萍,訴說其名字來歷的時(shí)候,旁邊坐著沒戲的侍萍也跟著站起來,表現(xiàn)內(nèi)心的波動(dòng)。這樣的設(shè)計(jì)打破了舞臺模仿現(xiàn)實(shí)的假定性和第四堵墻,拓展出另一重戲劇空間,也豐富了舞臺的表現(xiàn)力和人物之間的心理關(guān)系,相當(dāng)有意思。遺憾的是,除了讓周樸園就坐之外,這塊轉(zhuǎn)椅劃出的前臺似乎并沒有發(fā)揮出更多先鋒作用,而且,演員的始終在場偶爾也會導(dǎo)致舞臺走位的混亂,有一段正在演戲的角色和沒戲的演員同時(shí)在舞臺上游走,不明就里的觀眾還以為演出到此結(jié)束,這使本已有些破碎的敘事有進(jìn)一步瓦解的趨向。
宗教性的強(qiáng)調(diào):音樂與修女
這版《雷雨》有時(shí)似乎作者退場、意義瓦解,讓觀眾去思考和填補(bǔ)敘事層面的刻意斷裂。但有時(shí)作者意識或傳統(tǒng)表意結(jié)構(gòu)又極為強(qiáng)烈,這主要表現(xiàn)在全劇對宗教元素的極端使用:一是宗教音樂,二是教堂的兩位修女。如果有人將這兩者放在本版《雷雨》戲劇呈現(xiàn)的核心位置,甚至說成是真正的主角,或許都不為過:在極簡舞臺設(shè)計(jì)和雷雨聲都不出現(xiàn)的視聽控制下,密集的宗教音樂和修女形象分別從聽覺和視覺上對觀眾的舞臺感知、敘事視角和戲劇結(jié)構(gòu)的建立、演員表演的補(bǔ)充、乃至主創(chuàng)詮釋意圖的實(shí)現(xiàn)這四個(gè)方面都發(fā)揮著關(guān)鍵作用。

繁漪與周樸園的對手戲
曹禺在序幕中提示劇情發(fā)生十年后,周公館已改成教堂附設(shè)醫(yī)院,并使用巴赫的《B小調(diào)彌撒》和大風(fēng)琴音樂作為背景。本版演出除了這首彌撒,還用到莫扎特、威爾第的安魂曲等各種傳統(tǒng)宗教音樂。在每一幕的開始、結(jié)尾、轉(zhuǎn)場或沖突高潮的時(shí)候,宗教音樂都會響起。如此高頻度的使用確實(shí)在《雷雨》演繹史上前所未有。西方音樂里這些經(jīng)典彌撒、安魂曲等宗教合唱與管風(fēng)琴音樂,本身便是長期以來界定歐洲傳統(tǒng)日常生活與信仰活動(dòng)的藝術(shù)形式,這版《雷雨》對音樂的使用確實(shí)頗為獨(dú)到,能與劇情發(fā)展、人物心理相通,不僅奠定整體舞臺情緒和戲劇氛圍,偶爾也能起到表意作用,甚至還能增強(qiáng)表演力度,協(xié)助塑造人物。
如第二幕繁漪那段熾熱發(fā)狂的獨(dú)白:“當(dāng)時(shí)我就再掉在冰川里,凍成死灰,一生只熱熱烈烈地?zé)淮危簿退銐蛄?rdquo;這時(shí)莫扎特《安魂曲》里最為沉郁悲戚的段落《落淚之日》(Lacrimosa dies illa)響起,不僅用作轉(zhuǎn)場,也仿佛是繁漪一生悲哀的預(yù)示和祭奠。又如第三幕在杏花巷魯貴家,開場用威爾第《安魂曲》第一段里極盡哀婉與柔和的美好旋律,與四鳳這位無辜少女的角色特點(diǎn)相當(dāng)貼切,也像是對她的哀悼。第三例,周樸園在第一幕結(jié)尾宣告:“我的家庭是我認(rèn)為最圓滿,最有秩序的家庭”時(shí),巴赫的樂曲聲響起,莊嚴(yán)的音樂在此的作用值得咀嚼,似乎表明人物深陷虛妄而需要救贖的悲憫視角,又似乎預(yù)示后續(xù)家庭毀滅的殘酷。

修女配合周樸園的命令讓繁漪吃藥
與大量出現(xiàn)的宗教音樂相伴的,是頻繁參與劇情的兩位修女。在原作中并不起眼的修女,在此儼然命運(yùn)女神般時(shí)刻注視著人間注定的悲劇,與音樂同為創(chuàng)新而重要的表達(dá)形式。當(dāng)巴赫《B小調(diào)彌撒》無比沉重的第一段合唱“懇求主賜憐憫”(Kyrie)轟然響起,修女既見證各人命運(yùn),又如夢魘般籠罩眾生,音樂對之予以拓展強(qiáng)化,形成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戲劇高潮。
宗教音樂和兩位修女,都出現(xiàn)在原作里的序幕和尾聲,這兩段的用意正如曹禺本人在《雷雨》序言里所說:“我請了看戲的賓客升到上帝的座,來憐憫地俯視著這堆在下面蠕動(dòng)的生物……愈掙扎,愈深沉地陷落在死亡的泥沼里”。應(yīng)當(dāng)說,對宗教性的強(qiáng)調(diào)和觀眾上帝視角的建立,都符合曹禺編織在原作里的悲憫情懷和形而上學(xué)線索,在舞臺上突出這兩個(gè)元素也確有新意。但整體上未免過于密集,也過于倚重,當(dāng)這密集與倚重在劇中不斷重復(fù),原作本身的豐富立體,便逐漸被簡化為單一固定的模板,使作者預(yù)設(shè)的立場和觀念主宰并封閉了詮釋的空間,代替了舞臺上本應(yīng)是動(dòng)態(tài)發(fā)揮而開放鮮活的戲劇體驗(yàn)。尤其是兩位修女一直跟隨角色進(jìn)出,仿佛使勁摁著觀眾,一刻不停地在大聲重復(fù):這是命運(yùn)的昭示,這是渴望救贖的罪惡……

魯侍萍在兩位修女的尾隨下與周樸園對談
表演的爭議:費(fèi)解的第四幕
也許是宗教元素的過于強(qiáng)大,也許是反戲劇的主導(dǎo)思想,相比試圖創(chuàng)新的舞臺和濃郁的宗教色彩,全劇的表演反而顯得有點(diǎn)羸弱。
上半場前兩幕雖有繁漪、四鳳等人可圈可點(diǎn)的表現(xiàn),周樸園也可稱尚可,但已顯出冗長乏味的跡象。也許,演員的表演受到破碎敘事和極簡舞臺的影響,可能有些左右為難,表現(xiàn)出不太穩(wěn)定也不很清晰的狀態(tài)。一方面,傳統(tǒng)方式的情感爆發(fā)雖在繁漪、四鳳這里仍有效果,但在音樂、修女與其他在場演員共同設(shè)置的先鋒氣息和上帝視角下已顯得突兀、不協(xié)調(diào),另一方面又很難創(chuàng)造出新的表演系統(tǒng)去適配這個(gè)新的舞臺。
到下半場,演員自身狀態(tài)的不均衡開始越發(fā)顯著,魯侍萍、魯大海和周沖的表現(xiàn)確實(shí)不盡如人意,臺詞機(jī)械,表情僵硬,肢體幾乎沒有,缺乏本應(yīng)緊張密集的動(dòng)作和戲劇性,也沒有情感的爆發(fā)力,在實(shí)驗(yàn)性舞臺的集中烘托下更顯單薄,直到周萍與繁漪的對手戲才略有改觀,但在呆板的整體表現(xiàn)和缺乏配合的狀態(tài)下,繁漪展現(xiàn)瘋狂與神經(jīng)質(zhì)的正常發(fā)揮也略顯跳脫和過火。破碎化的敘事上疊加的是片段化的表演,沒來由、沒過渡、沒鋪墊,動(dòng)作缺乏連貫,情感顯得突兀。
第四幕的結(jié)尾,尤其令人費(fèi)解和失望。周萍開始脫離原著轉(zhuǎn)為搞笑的人設(shè),對繁漪的瘋狂采取漫不經(jīng)心甚至譏諷的態(tài)度。其實(shí)這里本應(yīng)是高度緊張的氣氛:經(jīng)過前三幕的鋪墊和發(fā)酵,經(jīng)過人物關(guān)系的揭曉,經(jīng)過痛徹心扉的臺詞和動(dòng)作,人物靈魂面臨重大沖擊、倫理與情感開始激蕩,逐步陷入自身難解的悲劇,但舞臺上卻非但沒有雷雨將至的沉郁深重,反而在周萍輕佻語氣的帶動(dòng)下顯得非常浮躁浮夸,觀眾也像看滑稽戲般笑場不斷。

第四幕,魯家一家三口與周萍坐在沙發(fā)上表演驚心動(dòng)魄的結(jié)尾
這時(shí),讓場面變得更加滑稽的是魯侍萍、魯大海、魯四鳳這一家三口索性全都坐在長沙發(fā)上一動(dòng)不動(dòng)而又飛快地背著臺詞,并與前臺轉(zhuǎn)椅上的周樸園一起觀看周萍坐在單人沙發(fā)上不停逗笑全場。大家在舞臺上同時(shí)吼出最后的臺詞,配合之前諸人漠然而混亂的走位,確實(shí)如有些觀眾指出的那樣,有股校園實(shí)驗(yàn)戲劇的觀感。
這時(shí),劇場內(nèi)突然一聲毫無預(yù)兆的巨響,昏昏欲睡的觀眾全被嚇醒,劇名中的“雷”總算降臨。不熟悉劇本的觀眾至此基本處于崩潰或放棄狀態(tài),熟悉劇本的觀眾也許會根據(jù)周樸園的臺詞進(jìn)度,感到周沖和四鳳應(yīng)該已在這聲晴天霹靂下死去?周萍也已經(jīng)死了?但死因不明。這時(shí),兩位修女當(dāng)著沙發(fā)上幾位死者的面上前讓繁漪和侍萍吃藥,這表示戲劇從第四幕行進(jìn)到了原著的尾聲階段,舞臺響起馬勒第二交響曲“復(fù)活”的結(jié)尾合唱,周樸園在修女的帶領(lǐng)下虔誠地念起《圣經(jīng)》,這時(shí),舞臺上還坐在沙發(fā)上石化的人應(yīng)該都已發(fā)瘋或死亡,唯一還能走動(dòng)的周樸園則靈魂得到拯救,并在大雪紛飛和馬勒浩蕩宏偉的音樂聲中獲得升華。

演員謝幕
人物的定位:重構(gòu)的尺度
早在演出剛開始的序幕中,周樸園就對修女說:“自己也想離開這死地方。有什么資格去厭惡別人?”聽到這句原著里并沒有的臺詞,已經(jīng)預(yù)感到周樸園的人物形象要被重構(gòu)了。這也是值得期待的創(chuàng)新,之前曹禺之女萬方女士的《雷雨·后》也曾試圖借原著留下的線索去發(fā)展周樸園的形象。但這也是頗具風(fēng)險(xiǎn)的嘗試,因?yàn)槿宋镆延屑?xì)密的塑造和嚴(yán)整的邏輯,要依靠表演重新詮釋并改造成功、獲得觀眾認(rèn)可實(shí)非易事。
下半場快開始時(shí),只聽得身后幾位女性觀眾在閑聊對本次周樸園的不滿,也頗為有趣。胡軍其實(shí)是一位需要導(dǎo)演雕刻的好演員。這次《雷雨》里的大家長加董事長周樸園,在他重新塑造下,顯得似乎壓力巨大、沉默內(nèi)斂、心事重重,面對瘋狂、任性的家人在竭力操持。在多次訪談視頻中,胡軍也強(qiáng)調(diào)周樸園的艱辛不易和癡情專一,這樣的詮釋令人頗為錯(cuò)愕。
看來確實(shí)需要“回到曹禺”。在原作中,周樸園為了得到大筆結(jié)婚陪嫁,殘忍拋棄發(fā)妻侍萍和出生三天的兒子;為了撈取巨額保險(xiǎn)金,故意讓江堤出險(xiǎn)淹死2000多名童工。在家中壓迫妻兒,在社會鎮(zhèn)壓罷工,殘酷下令開槍打死三十名工人等。這些暴行使他在罪惡的泥潭里愈陷愈深,難以自拔,最終目睹自己曾經(jīng)牢牢掌控的家庭從崩裂到毀滅的結(jié)局。

周樸園人物形象得重構(gòu)
1920年代的中國,現(xiàn)代工商資本的利益邏輯開始與傳統(tǒng)儒家倫理的尊卑規(guī)則相結(jié)合,形成有封建特色的資本統(tǒng)治形式和觀念形態(tài)。在第一幕,位于權(quán)力鏈頂端的周樸園非常得意和滿意他口中“最有秩序的家庭”,因?yàn)樗坪醴先寮覀鹘y(tǒng)規(guī)范:父子有親、長幼有序,主尊下安、貴賤有等。對這種至今還在有人推崇的傳統(tǒng)倫理秩序,曹禺敏感地發(fā)現(xiàn)在其和諧理性的虛偽表象下,掩蓋著無數(shù)原始野性的墮落與罪惡,每一個(gè)人身上都似乎帶有著被欲望和激情灼燒的原罪,也時(shí)刻都在煉獄里掙扎和挑戰(zhàn)著倫理綱常。
《雷雨》的悲劇,正是通過一個(gè)個(gè)人物的掙扎、反抗和最終毀滅,揭露和沖擊著現(xiàn)代資本邏輯與傳統(tǒng)封建倫理成功結(jié)合、至今不衰的堅(jiān)硬外殼。周樸園精心維持的產(chǎn)業(yè)和家庭,以及他那成功企業(yè)家、丈夫和父親的完美人設(shè),都受到劇中人的沖擊:魯大海反抗他資本家的殘酷和草菅人命,繁漪反抗他道貌岸然的虛偽與控制囚禁,但這些波動(dòng)又都被他嫻熟的操作消弭。年僅23歲的曹禺對這煉獄世界的圖景確實(shí)無法解答也無力解決,因而在劇本中以訴諸宗教,訴諸原罪、救贖等基督教文化意識的方式去應(yīng)對這些深層的矛盾與困境。
因此,曹禺借序幕和尾聲的設(shè)置,希望觀眾能用超出角色的更高視角去審視這個(gè)表面光鮮道德、內(nèi)在墮落不堪的索多瑪世界,用宗教性的悲憫情懷去看待包括周樸園在內(nèi)的深陷欲望與罪惡而難以自拔的蕓蕓眾生,這種理解當(dāng)然是恰當(dāng)?shù)摹?/p>
從妻子獲取第一桶金并成為如今人人羨慕的優(yōu)秀企業(yè)家與成功人士之后,周樸園時(shí)常陷入孤獨(dú)和空虛,總預(yù)感將“有什么可怕的事發(fā)生”,這當(dāng)然也符合原作的設(shè)置。但如果就因?yàn)橹軜銏@面對自己的罪惡常有幾分惶恐不安,對無情拋棄的妻兒有保存相片的舉動(dòng),就因?yàn)樗侨珓∽詈蟮男掖嬲撸湍軐⑦@個(gè)人物重新詮釋成社會與家庭的中流砥柱和癡情專一的道德標(biāo)兵?進(jìn)而用理解和支持的姿態(tài)去表演他作為當(dāng)家人的無奈艱辛與不易,甚或是以同情甚至欣賞的態(tài)度去重構(gòu)周樸園,讓他最終獲得解脫、救贖乃至升華?恐怕這在原作中并不存在,也并非曹禺的本意。

周樸園人物形象的重構(gòu)
主創(chuàng)不僅在訪談中反復(fù)強(qiáng)調(diào)周樸園的艱辛不易,對其他人物也大都有顛覆性的定位和重構(gòu)。如對魯侍萍的設(shè)定,從長期以來的下人身份轉(zhuǎn)為突出身穿旗袍的貴婦氣質(zhì),她的兒子煤礦工人魯大海則被塞進(jìn)一套波西米亞風(fēng)的休閑西服小套裝,還加上黑邊眼鏡,變成一位充滿小資情調(diào)的大學(xué)生。魯大海成為小資青年之后,其舞臺面目自然開始模糊,與身邊的周沖無法區(qū)分。而最難小資化改造的底層人物魯貴則干脆直接刪除,喪失了舞臺上的可見性。原作中非常顯著的階層對立狀況和不穩(wěn)定因素就不再存在,《雷雨》因此走向某種1990年代以來常見的豪門恩怨劇或?qū)m斗劇模式:皇帝或老爺慈愛操勞、后宮或太太間愛恨情仇、子女們則胡鬧任性。也正如那些影視作品一樣,都固有而內(nèi)在地缺失了社會歷史意義上真正的現(xiàn)代意識或現(xiàn)代性,而這點(diǎn)恰是曹禺在原作里的探索和追尋。
如此一來,表演里大量別扭、費(fèi)解和突兀的地方也就不再難以理解:曹禺筆下殘忍的宇宙或命運(yùn)、動(dòng)蕩崩解的倫理秩序與激烈的情感沖突大都在以反敘事為表象、反意義為核心的狀態(tài)中被淡化,成為一個(gè)中產(chǎn)群體內(nèi)部的故事。因此,人物的表現(xiàn)也當(dāng)然會有股冰冷和平靜,與曹禺原作中銘刻在人物靈魂里的“郁熱”氣質(zhì)格格不入,于是無怪乎當(dāng)侍萍得知女兒四鳳與少爺有身孕時(shí)依然沒有太大反應(yīng),繼續(xù)保持那股冷漠淡然,類似細(xì)節(jié)構(gòu)成的整體風(fēng)格有了邏輯基礎(chǔ)。不知這樣的基本設(shè)定是否出于主創(chuàng)對當(dāng)下觀眾群體的用戶畫像和市場定位,但確實(shí)符合許多中產(chǎn)群體在自我理解和價(jià)值追求上熱衷或標(biāo)榜的隨和優(yōu)雅與穩(wěn)定超然。
總而言之,這次《雷雨》的探索和實(shí)驗(yàn),其實(shí)頗為用力,又破又立,有力求創(chuàng)新的呈現(xiàn),也有強(qiáng)調(diào)差異的理念,還有人物形象的重構(gòu),宣傳“回到曹禺”之類其實(shí)大可不必。但形式追求和內(nèi)容呈現(xiàn)又有些割裂和潦草,介于創(chuàng)新與傳統(tǒng)之間的表演也有些尷尬和粗糙,看似難以找到內(nèi)在的力量與貫通的線索,實(shí)則大多是重構(gòu)人物時(shí)的去階級邏輯與原作發(fā)生一定程度的沖突而使然。雖然經(jīng)典確實(shí)具有任憑魔改都能屹立的空間,但既然以《雷雨》的劇本基礎(chǔ)決定了消解敘事、消除意義很難徹底實(shí)現(xiàn),那就依然需要在創(chuàng)新時(shí)審慎考慮表演連貫、尺度得當(dāng)?shù)那逦尸F(xiàn)。
所以,從《雷雨》的整體把握出發(fā),在更好駕馭原作的文本特性和考慮觀眾的接受慣性基礎(chǔ)上,如何在舞臺上達(dá)到追求新異與更新傳統(tǒng)的平衡,如何在人物形象的理解上更準(zhǔn)確地把握求新求異的限度,都仍有探討的空間。也許我們可以期待在未來,經(jīng)過嚴(yán)密整合、細(xì)致協(xié)調(diào)和反復(fù)調(diào)教下,這版《雷雨》能取得更好的成績。